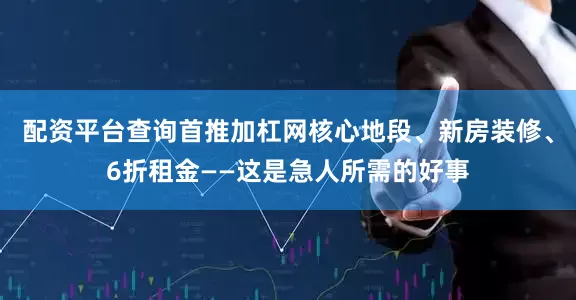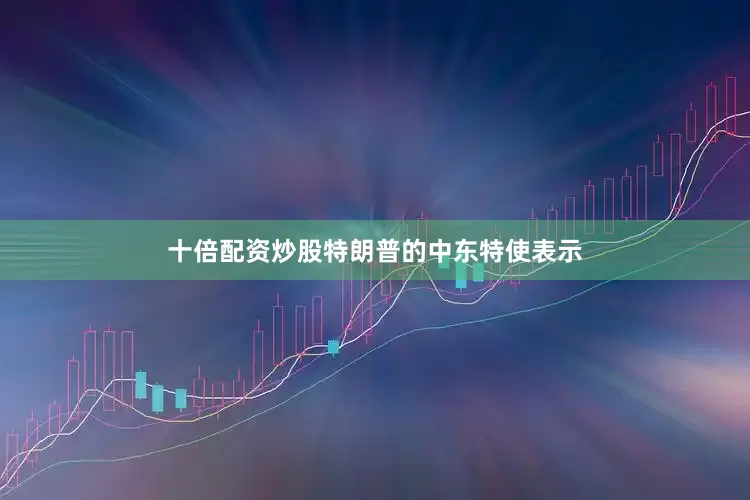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罗一茜
不少专业学者的写作,从学术生产转向为大众写作,成绩显著。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正宏就是其中一位。他所写的“陈正宏讲《史记》系列”深受普通读者欢迎,目前已推出《时空:〈史记〉的本纪、表与书》和第二部《血缘:〈史记〉的世家》。他所推出的《史记百句》更是以中小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。
在当下正在举行的上海书展上,陈正宏携该系列最新作品《众生:〈史记〉的列传》为读者做了一场分享。

陈正宏教授
向司马迁学习:
写文章既要“天花乱坠”又要有文献支撑
《众生:〈史记〉的列传》出版人、中华书局上海聚珍总编辑贾雪飞在现场透露,就在8月13日上海书展开幕当天,陈教授在《文汇报》发表了一篇文章谈《史记》。文章不长,1500字左右,但收到了各界热烈的反馈。这篇文章提出一个问题:《史记》最初是一部独立的著作吗?这篇文章本可以在学术刊物发表,但陈教授却放弃了,而是发在覆盖面更广的大众媒体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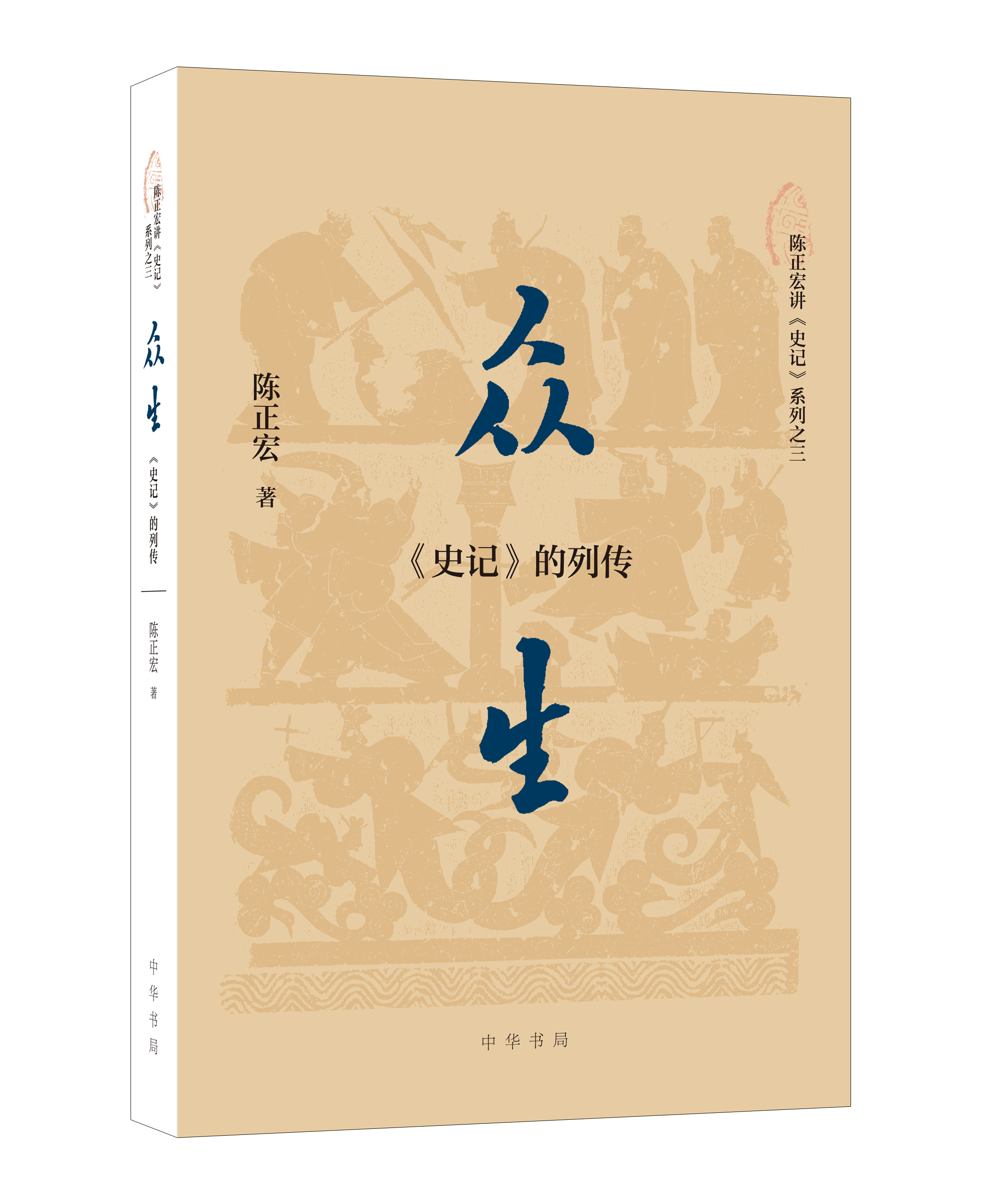
《众生》
从学术体系写作到大众写作,看似更简单,但陈教授却认为,“非常难,有时候就像人格分裂一样。虽然我的硕士论文是用文言文写的,但我感觉写普及文章比写专业论文难得多。一部分学术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论文游戏,现在写的这些通俗读物,我是以之为荣的。小众的学术能够让大众懂,然后能让他们去读原著,在我看来是光荣的。写文章既要写得‘天花乱坠’,背后又要有文献作支撑,在这一点上,是司马迁教了我。”陈教授总结说,真正会讲故事的,是要懂得这中间的分寸的,分寸感是最难的。

新书分享会现场
《史记》最初可能不是一部独立的著作
《史记》最初是一部独立的著作吗?这个看似已经答案很确定的问题,却在陈教授心头萦绕十年了。陈教授的本业是文献学,他一直在想,从孔子时代到刘向刘歆父子的《别录》《七略》,这中间就没有目录学吗?人民大学的徐建委教授提出《史记》是“因书立传”,意思是写先秦诸子的几篇,是司马迁就着当时能看到的各家子书来写的,所以《左传》虽有不少诸子故事,《史记》列传却很少引用。陈教授受到启发,并进一步推测:不光是先秦诸子的那几篇传,也许七十列传的大部分,都是“因书立传”,只是这其中的“书”,不一定都是后世理解的比较狭隘的已成一部书的“书”,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用文字书写的个人或特定群体的文献,包括之前的家族谱录、个人传记、官员档案等等。

见面会现场嘉宾合影
陈教授说,“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”,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太史令的职责,是主管天文历法,兼管文献档案,所以父子俩“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”,最初的工作,是把掌握的文献作一个基础的分类,并写出具有独创性的提要。那么什么时候变成了独立的著作?就是李陵事件。这之后,司马迁的生理、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同时被汉武帝提拔为中书令,能够看到的文献档案更多了,这时就有了写一部自己著作的想法。陈教授坦陈,这中间猜测的成分比较多,还需要很多复杂的论证,可以写成专业的学术文章,但想让更多的人看到,引起更多的讨论,还是更愿意发表到大众媒体上。
(中华书局供图)
东南配资-东南配资官网-网上配资炒股-大的配资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